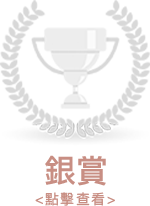有一天,如果指揮官將手中的筆當成了槍,
並將對戰術少女的情感化作彈藥的話,這將會誕生出怎樣的火花呢?
銀賞作品 ——《春田的酒吧軼聞》
作者:新德
簡介:
格里芬剛組成的肯巴利小隊第一次任務就遭逢變故,小隊沉浸在無以復加的沮喪裡。
此時,隊員其中三人:卡爾卡諾M1891、FN49、卡爾卡諾M91/38依序來到基地裡春田的咖啡廳。
用大相逕庭的角度說了同一個故事。
《春田的酒吧軼聞》羅生門之鑰
我捧著拿鐵,輕輕吹動上頭飽滿的熱氣。
店裡很靜,僅剩偶而睡醒的冰箱嗡嗡的哼著。
吧檯邊緣的客人壓低眼簾,以為這樣便能藏起自己。
我不打擾他。
世上有太多不願提起的故事,令人恨不得遺失在哪一次放空的等待裡。
我小心翼翼抿了口咖啡,奶泡與上唇綿密的觸感,暖烘烘的拖著腦袋,成功復甦凍僵的思路。
我閉上眼睛,想像細緻的泡泡是呵護記憶的容器,那些真情流漏的字句掙脫透明薄壁,再次提醒我這一切的起因。
我想跟你談談稍早的兩位客人。
傷痕累累的兩位客人。
我放下槍選擇在格里芬咖啡廳裡用滾水畫圓,已是數個月前的事情。
能有射殺以外的辦法支援同伴是件美事,我很享受研磨咖啡、端出酒水。
如果可以,也歡迎你來店裡坐坐。
尤其在這種梨花帶雨的冬季,我抹去室內玻璃窗凝結的水霧,外頭雨不大,但不肯停。
店鋪掛門風鈴驀然唱了起來。
記得今天是全員出勤的日子,這個時候空閒的除了高官。
就是傷兵。
我回過頭去,望見推開門的那雙手。他的袖口彷若陽光蓬鬆的純白花朵,風雅工致的針線活層層展現自製服裝者細密的心。
「春田太太!」他咧嘴,大喇喇揮手,對身上的包紮豪不介意。
「『英雄』卡爾?」是卡爾卡諾M1891。
「哈哈哈,你看我現在這樣,別那樣叫我啦。」他刻意抬起替換成義肢的左手,用沒有皮膚的裸露金屬手指在鼻子前擺出趕蒼蠅般的無奈動作。
「傷的很重呢,沒問題嗎?跑來這裡。」我替她拉開吧台座椅,她自製的軍服燙的巍巍峨峨,上頭的金屬飾品也被保養的精神奕奕。
「修復室待第二天啦,趁他們在做新的手臂時溜了出來,想喝酒!」卡爾露齒笑,坐挺身子。
「我們晚上八點後才開始賣酒,而且傷患怎麼可以喝酒。」我邊說邊遞上熱水菜單。
「我們是人形,修一修就會好了,好嘛春田,我幾乎剩飲食模組是健全的。」他在頭頂擺出雙手合十的拜託拜託。
「真是的,只能喝淡的喔。」我莞爾,被逗樂了。
「太太人最好啦,spumoni,謝謝。」他也笑了,渾身散發英挺的魅力,找不著絲毫傷者的陰鬱。
這下反而讓人好奇傷是怎麼來的了。
「知道付款方式嗎?」我繫好圍裙問道,這裡說是付款卻不收錢,挺異常的。
「知道知道,提供一個自己的故事給你聽,對吧。」
「我就跟你說說我怎麼躺進修復室的。」他指著包紮的左眼。
收起笑容。
格里芬與鐵血纏鬥的越發越疲弊,為了填補捉襟見肘的戰力,上頭逐漸將駐守邊區的人形調回前線。
我卡爾卡諾M1891便是其中之一。
拜別負責數年的T02區雖然可惜,但幸虧先前積累的功勳,我很快又有了自己的小隊。
以我為首、我妹妹、馬卡洛夫、FN49,臨時成立,暫稱肯巴利小隊。
所謂累積的功勳,得從「英雄」稱號說起。
T02區僅憑我率領的狙擊手小隊,在資源寥寥無幾的條件下達成全區肅清。
因此流出眾多加油添醋的穿鑿附會,我也為人加冕英雄。
這其中我能向你拍胸脯確信的是,我的小隊的確非同凡響。
但一個強大的團隊,最運籌帷幄的常常並非領頭羊。
因為首腦不一定是倚賴機關算盡的智力得以黃袍加身,更多時候是夾帶毫無道理的領袖魅力。那是更本質更深處,得天獨厚的天選氣息。當然,辨識人心、適才適所等技能還是基本必備的啦。
這種上帝垂青的人格特質,讓你發號施令多數人將服從拜服,現在想想,真像魔法一樣。
所以說,領頭者並不是最足智多謀的,將頒布的綱目細細分工,疏通矛盾付諸實行,細膩嵌合齒輪的人物,才是組織中真正辦事能力最高的。
也就是二當家。
所以說你發現公司指揮各位老將作業的是老闆毫無歷練的無能外甥時,你真該趕緊逃難。
扯遠了,我的意思是,我在T02區率領的成員之所以所向披靡,乃是我隊中的二當家一手打造。
也就是我妹妹,卡爾卡諾M91/38。
由於部隊中沒有其他源自杜林兵工廠同系列的兵械,我們便私自分用這個名字,我是卡爾姐,她是卡諾妹妹。
卡諾與我不同,成長歷練沒有彩光擁簇。我就像代表組別上台拿獎狀合照的模範生,而團隊功臣的他卻在無人留意的角落拍手,掩埋在掌聲中。心思纖細的她吃了很多苦頭,甚至養成愛說謊的惡習,但與她資訊情報的接收能力相比,也僅是瑕不掩瑜。
常常覺得她與我能見的世界不大一樣,比方說現在我對咖啡廳的描述會是:心神寧靜的棕色,空蕩蕩的上班日午後,粉橘的spumoni口感層次舒適,耐心聆聽的春田太太和善親切。而我的妹妹很可能接收到的是:座位數量、酒牆上的酒種分類邏輯、判斷菜單上的推薦品項是味道最有自信還是利潤最高、注意其餘賓客進出的臉色辨識自己是否佔用了常客私心認定的王位坐席。還有太多太多,是我根本揣摩不出的。
她目光具備的入微滲透力,使我也經常參照她的分析執行命令。另外如你所見,鬱鬱殷殷、嘴硬又厭世卻依然為他人努力的身姿,簡直可愛極了,對吧,對吧!
阿,不小心曬妹妹了,來談談這次任務。
肯巴利的首支命令是無聲無息狙殺S09區巡邏中的鐵血偵察部隊,這種斥候不會配備強力武裝,對於只利用模擬訓練磨合的全新隊伍來說是一次很不錯的實戰開場。
S09區廢棄都市大樓林立,對狙擊手來說,就像把小丑魚放回海葵花群裡。
第一天,格里芬能夠出借的器材短缺情況下,我們還是如火如荼狙殺了約定的數量。在制高點扣板機跟在沙發上按遙控器一樣輕鬆寫意。
初戰告捷的糖衣蒙蔽了我對危機的嗅覺。
所以當我察覺現場資訊與格里芬匯報的多有出入,鐵血的先遣隊數量顯然多於預估時,我任性的倚賴能夠私自做出判斷的權限,將小隊留了下來,順手打掃打掃。
於是我失手了。
陰天,頭上的雲比我身邊的水泥塊還沉。
我們分成兩隊,在兩個定點分別觀察殘餘的敵軍確切數量。
「那是夢想家嗎?」FN49單眼貼著瞄鏡,不可置信。
「掃地也能掃到支票。」我齁齁,透過望遠鏡找到鐵血部隊層層守護的身影。
我的腦袋只兩項直覺,打?不打?
這是力能所及的目標,擊殺夢想家也能即刻令陌生的前線部隊驗證來自T02區的傳說,快速建立品牌。要是成功,那孩子也能少聽一點閒話吧。
值得一試。
擒賊先擒王,狙殺夢想家後,他的部隊肯定大亂,接下來要用什麼辦法將他們引導至卡諾的狙擊範圍裡,真想聽聽卡諾的建議。
我還在盤算轉移到更優秀的狙擊地點,夢想家卻猛然擺手指揮起來,他的部隊氣勢凌厲,四射爆散如毒針一般撲天蓋地的搜索。
這顯然與昨天公式化的巡邏斥候不同,他們有明顯目標在偵查什麼。
我們明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下也沒得選了,來不及聯絡在另一端埋伏的卡諾與馬卡洛夫,格里芬沒能借我們些不會受干擾器損毀的通訊器材。
夢想家忽地直朝我們藏身的廢棄大樓迫近。
怪了,戰場上野性的直覺嗎?很快我們就會在熱感應器的探索範圍裡。一眨眼的,情況轉逆為爭分奪秒的最終死線。
多想無益,準備好扣板機。
「怎麼會這樣!」FN49驚慌失措。
「沒事!相信我,把濕度溫度風向風量今日的沙塵狀況所有情報說出來!」我從容熟捻的架起槍枝,透過瞄鏡跟著夢想家的身影。
FN49吞吞吐吐,但我沒有聽不清楚的部分。
我凝神,封閉聽覺嗅覺,將單眼捕捉的性能推向頂點。
我能感受目標的呼吸吐納、我能數出她脖子上的金屬有幾道細痕。
她停下腳步。
天時地利,扣下板機。
子彈撕開灰色的天空,拖著金黃的尾巴,以迫不急待送目標下地獄的氣勢全力奔馳。
然而。
子彈在夢想家面頰刮出血煙。
夢想家緩緩轉過頭。
眼瞳收縮,目光凌厲,令我產生雙方貼額互視的錯覺。
時間暫停。
腦袋塞滿劈哩啪啦的驚嘆號。
臉頰與眉心對狙擊手來說簡直城南城北,我居然會失手。
我欸,我卡爾卡諾M1891!
所有的一切,居然要毀在這發子彈裡。
是我太自大了嗎?
我下意識使用烙印系統重複檢查槍枝的校準狀況,還真的以為世界為我靜止。
冷汗逃難般鑽出背脊。
我本能將FN49拍開,身子一涼,我的半邊軀體已壟罩在夢想家手中殺器噴出的光瀑裡。
「啊啊啊啊!」
我扯開嗓子,以痛為推力,將汙濁的疑惑、雜念、與懊悔,以向天質問的力道吐了出來。
我砸向地面,暫時讓疼痛接管身體,耐心調整呼吸。
啊!可惡!
好痛阿!
劇痛在神經元裡暴跳咆哮,幾乎要煮沸腦漿。
思緒黏糊糊的。
但我不會倒在這裡。
「站起來,FN49!」我咬牙,竭盡全力起身。
隊伍還需要我的指揮,得先讓他們撤離。
「跑,通知我妹妹,通知卡諾,撤到第一天的紮營地點。」
「你呢?」她擠出聲音。
「我會持續開火,營造主力部隊全在這裡的假象,盡可能修復通訊雷達,之後再跟你們聯繫,快點,還發呆啊!」我想都沒想,唇舌有如導航自動組成字句。
FN49聽令衝出,我也放寬了心。
廢了隻手,槍都架不穩,身體眾多機能模組瀕臨崩潰,但我能扣板機。
我開始朝敵軍胡亂開火。
將鐵血的目光釘在這裡,FN49與卡諾他們才能順利逃離。
彈藥用鑿,不曉得是多久後的事。
「上次備份心智雲圖是什麼時候?」我跪了下來,思緒恍惚。
槍炮聲響撲朔起來,我開始疑惑自己與地板間的距離。
模糊的空間感甚至令我產生凌空漂浮的錯覺。
可惡。
真不想忘記妹妹的一顰一笑,儘管是有所隱瞞的表情。
她平安逃掉了嗎?
訊號還是壞的嗎。
至少想把信息傳出去。
別等我了,我到不了。
卡諾。
「G11,去樓下把守,一隻都不准放上來。」
我像是隔著水面聽見這陌生的命令。
「為什麼又是我去前線。」
「9,跟著她,別讓他偷懶。」
「好呦!」
「416,這個距離投彈你有自信命中嗎?」
「貓抓未睜眼的幼鼠會撲空嗎?」
「你是貓的話,一定是臉很臭的波斯貓。」
聲音越來越近,我試著摸索暗藏的戰術刀。
「嘿,沒事了,M1891。」她一手按住我的手腕。
「解釋太麻煩了,安心睡吧。」
另一手向我後頸送了記俐落的手刀。
「然後就是你知道的了,在修復室醒來,得到兩天假,還能在這裡跟你說故事。」卡爾笑的爽朗,眼神清澈,甚至沒有閃過任何受挫的雜質。
「辛苦了,今天可以好好在店裡放鬆喔,有什麼需要的儘管跟我說。」也許卡爾就是堅毅的代名詞,我能做的,就是替他空出個充電插槽吧。
本來是這樣想的。
「我說春田阿,正常來說新組的小隊馬上嘗到失敗都會非常沮喪吧,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沒辦法記得哀傷多久,不過真要檢討,這次失敗果然要算在我頭上。」卡爾臉一沉,身上閃閃發亮的掛飾勳章都歛起光芒。
「是我的錯。」他緩緩閉上眼。
「驕矜必敗,我自豪的狙擊技術毀了自己,毀了團隊的信心。明知現場資訊與事前調查資料多有模糊闕漏,卻不肯撤離,才會在第二天碰上夢想家,搞的措手不及。」
「要是我的隊員因此沉浸在負面情緒,我也會無法得救。」
「但是,由我去接觸在情緒上頭的對象只會得到反效果。」
「好在我挺會看人的,我知道有個好傢伙很適合幫我。」他睜眼,臉龐再次揚起颯爽的風。
卡爾將酒一飲而盡,看著我。
我總算理解為什麼卡爾說需要幫忙。
FN49像隻豎起寒毛的栗鼠,要是伸手碰她她肯定跌下座椅。
毛躁的亂髮,單邊上翻的衣領,皺褶略多的貼身背心,那是好陣子沒有換下來在床上躺著不動的痕跡,甚至也不在意勾破的絲襪。有的時候放棄自己,很容易展現在外表上呢。
我忍住好幾次想上前幫忙打理的小小衝動。
究竟為什麼卡爾的失誤能給他這麼大的衝擊?
「喝什麼?」
「內格羅尼。」
「知道怎麼付款嗎?」
「卡爾要我來的,她到了嗎?」
「還沒,知道怎麼付款嗎?」
她茫然,我向她解釋收費方式。
「故事?」她眼裡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也許你可以跟我說說發生了什麼事。」我與她禮貌的四目相交便自然移開視線。
不要壓著她,給她一點空間。
我專注於鑿冰球,假裝是順道聽個故事。
沉默良久,她開口。
「你知道我為什麼離開FN小隊嗎?」
暫時脫離FN小隊是為了鍛鍊。
我其實知道的,我在FN小隊裡與其說是負責掩護狙擊,到不如說是收收殘兵。
畢竟有菁英FAL和57,二星評等的人形沒有只做雜務也算不錯了。
這樣真的好嗎?我覺得自己一直在被淘汰的邊緣裡。
碌碌無為的不安感是我的心頭刺,換一個日子翻一個睡姿都隱隱生疼。
我其實也有憧憬的阿。
我想得到三星評等的肯定。
哈哈,很渺小嗎?但能得到跟大家一樣品質的火控核心就是我的夢想了。
也有人笑我市儈吧,但就像人類會以社經地位來評秤作為人的份量,我們人形也會直接以星等量化高低。
這是心照不宣的事實,汲汲追求功勳也是沒辦法的。
於是我報名了如雷貫耳的「英雄」卡爾小隊成員甄試,還真的讓我加入了。
沒有狙擊手不嚮往她的射擊能力,光是站在她身邊就讓我沉浸自己已經強一個檔次的幻覺裡。
「今後要請你多幫忙了。」卡爾伸出手,嘴角閃著星星。
「是,是!」我誠惶誠恐雙手抓住,像面試第一份工作般慎重。
就連我這樣的人,也能有天像卡爾這樣,意氣風發,提攜弱小嗎?
答案是不可能。
在與隊員一同模擬訓練的日子裡,我竭盡腦力要理解戰術配置、我窮盡專注要連續射擊,最後不要說差強人意,根本晴天霹靂。
每在崇拜對象面前出一次醜,你都覺得自己的心被撕下一塊無以名狀的重要東西。
「別在意!我來做你的觀測手。」卡爾信心十足,拍拍我的肩,力道沉猛。
她不知道這樣的力道對破爛的二星機體是種負擔,就像她不知道我其實根本已無能為力。
這就是無法觸及的強大吧。
我對卡爾產生了疏離感,但這種疏離感並沒有讓我看破功勳與人形價值間的關聯,反而化作餌食,我越來越渴求她回頭看我。
於是我什麼都做。
「我去借就好!」我舉手,至少想要有點功用。
「麻煩妳了,明天是我們第一次實戰,每個細節都至關重要。」卡諾點點頭。
卡諾沒有耀眼的光芒,但撇見她的射擊成績一樣讓我憔悴。
卡爾與卡諾,還有判斷老練的馬卡洛夫,每每射擊訓練結束,他們擦著汗討論屬於強者國度的詞彙,就像看原文書譯本,每個字拆開看我都懂,組在一起卻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我聽不懂,我跟不上。
我的自尊一點一點稀釋在自我演繹的陪笑裡。
悲劇沒有結束,慘澹的事件乘著無法停止的礦坑車,向無涯的底部探去。
「剛剛軍方全都借走啦!剩一些老設備,要用嗎?」格里芬租借設備的部門人員低頭寫著單據,連看我都不肯。
「麻煩了。」
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你也許認為設備不足不是我的問題,但我覺得我的無能已經化作靈氣,影響著每個事件的成敗。
哈哈,還真是看得起自己。
「只借到這個。」我覺得口乾舌燥。
卡爾端看設備的每一秒,都讓我隨時想找洞鑽進去。
是,我就是連這種小事都辦不好。
「看來格里芬真的是越來越不妙啦,我們明天要好好表現啊!」卡爾哈哈,清點完畢,交給卡諾做二次確認。
「請交由我來搬運!」我低下頭,像隻摔壞花瓶的狼狽小狗。
「那就麻煩你啦!」卡爾大方應允。
我說了,悲劇並沒有結束。
第一天,卡爾與卡諾換手連狙了六支鐵血梯隊,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也是我望塵莫及的成果。我光是背著笨重器材就夠折騰,跌跌撞撞。其後發現區域內還有剩餘的敵軍,決定留下來進行第二天的掃盪作戰。
第二天,我們意外遭遇夢想家,情勢所逼,卡爾要我報出氣候細項,決定主動射擊。
然而。
子彈在夢想家臉上刮出血煙。
夢想家緩緩轉過頭,面向我們。
周遭靜了下來,視野如負片效果般黯淡。
我低頭看著手中的氣候細項側量儀,面板數字飄忽閃爍,像躲躲藏藏的竊笑小丑。
是昨晚紮營不小心摔到那時嗎?
為什麼我沒有在射擊前先檢查儀器狀況呢?
為什麼是無能的我配在英雄身邊呢?
罪全在我。
我揪著胸口,想大聲道歉。
卡爾卻回身一掌拍在我胸膛上。
就一瞬間,世界幾乎靜止,我茫然向後傾斜,斷垣殘磚崩毀,無數瓦礫破片攻勢凌厲的刺向我們,我妄圖伸手抓住卡爾,卻見她半邊身子吞噬在夢想家的光束砲裡。
卡爾五官擴張,扭曲。
「啊啊啊啊!」
沒有什麼比英雄的慘叫更令人恐懼。
我看著她瞳仁內的英氣被焚燒殆盡,連同我僅存的希冀一齊散落凋零。
我跪了下來。
粉霾飄降,那戰場汙濁的雪鋪蓋在卡爾抽搐的軀體上。
我本能以跪姿緩緩向前爬進,撇見她焦黑的皮膚,立即顫慄的反向彈開。
我蜷縮起來,用盡全力躲進誰也找不著的黑色裡。
心懷憧憬是什麼笑話?
早點交出火控核心去端盤子當個小人物就好,上戰場逞什麼能?追什麼夢?
自始至終,我不過是個連三星評等都勾不著邊的貨色。
「站起來,FN49!」卡爾聲若宏鐘。
我抬頭,不可置信。
他睜不開左眼,左手與其說無力擺盪,倒不如說暫時還黏在肩膀上,需要倚賴槍枝作拐才能站穩身子。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你還站得如此挺拔?
「跑,通知我妹妹,通知卡諾,撤到第一天的紮營地點。」
他堅定的語句依然乘載著豐沛的英氣。
「你呢?」我整理紊亂的氣息。
「我會持續開火,營造主力部隊全在這裡的假象,盡可能修復通訊雷達,之後再跟你們聯繫,快點,還發呆啊!」她依舊高大,對自己的傷勢毫不在意。
我轉身,提氣狂奔。
也許他的傷並沒有這麼重?
我順著破孔依序跳下樓層,並撞開四樓的殘磚破瓦縱身一躍。
碰!
堅實地面回彈的力道震的我每一處傷口都恣意咧嘴狂笑。
好痛。
我哭了出來。
卡爾的傷明明比我要來的重。
我試著抹掉臉上的狂風暴雨,踉蹌向卡諾所在地跑去。
求求你,戰場的神。
請你救救卡爾。
「救救我阿!」
「沒錯,是我害的,很可笑吧。」他渾身哆嗦,抓著酒杯,手裡腥紅的酒液濺上虎口。
我繞過吧檯捏著紙巾前去擦拭,只見他嚇的驚弓彈起,酒杯與她的防衛碎了滿地。
在她道歉前我率先捧住她的雙頰,刻意晾在滾水旁的雙手烘的火燙,希望能給她些能量。
「FN49。」我將臉湊向前,讓我們鼻子貼鼻子。
這種時候,再怎麼安慰事情不是他造成的也沒用吧。
所以。
「你知道幽默感怎麼來的嗎?」我說,閉上眼睛。
幽默的培養是很看機緣的。
你可以觀察身邊那些談吐風趣,在團體中帶氣氛比較成功的人,沒有一個是優渥的環境培養出來的。
一個都沒有。
他們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曾經經歷重大的人際關係挫折。
他們為了避免再次體驗到相同的痛苦,下意識在人群中營造快活的氛圍。
所以人家說幽默的人大多很悲傷,就是這個意思。
不只幽默感,包容力、危機處理速度,這些都是在陰溝裡培養出來的。
這些特質強調痛苦的經驗,打磨出獨特的魅力。
正在培養它們的人卻是最缺乏關愛的,他們沒有大量的成功經歷去支撐,往往在抉擇點上表現的徬徨又恐懼。
他們非常缺愛。
而這些真正缺愛的人才真正有資格被人呵護在掌心上。
至少我是愛他們的。
「FN49,你現在過得很掙扎。」
「但不要害怕。」
「你的痛苦是你的門票,跟那些家世顯赫的人不同,跟溫室呵護的色彩不同,你能得到他們永遠不會有的魅力,不要害怕,硬著頭皮闖下去。春田在這裡支持你。」
我緩緩拉開兩個臉蛋的距離,望見她乾涸的眼眶再度迸出甘雨。
「再努力一下?」我問。
她將額頭輕輕靠上我的肩膀。
咬緊牙根。
「我會變強的。」她恨恨地說。
緊握拳頭。
「我會變強的!」她哭吼。
沙漠裡的仙人掌再次綻開花朵。
常常人遇到苦難,只是需要另一個人的關懷補上心頭碰出的缺口。
大家都很寂寞,而社會無形的壓力終會使壓抑的情緒變得奇形怪狀,連自己都陌生自己。
FN49也是這樣。
戰術人形的意義就是立下戰果,他發現自己越是遠離這個核心概念就越是惶恐,他開始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祿,還以為是自己打從心底的憧憬。
但我不會引導他停止,因為人越是接近社會邊緣就越趨近自我毀滅,他必須向社會訂立的中心思想靠攏才能安心,這也是大多數人無可奈何的事情。
也許背離戰場,只知道煮咖啡,停止殺敵,給同伴擁抱的我,才是異常的戰術人形。
但若是不想活在別人制定的規則下,也只好試著畫出自己的小小區塊,在裡面扮演著主導者。比方說克魯格選擇創業。
而我,選擇成為小小咖啡廳的小小店長。
至少這裡,我也能有我的小小規矩。
決定進什麼貨,選擇善待客人的方式,甚至任性的私自替自己泡杯咖啡。
我捧著拿鐵,輕輕吹動上頭飽滿的熱氣。
店裡很靜,僅剩偶而睡醒的冰箱嗡嗡的哼著。
吧檯邊緣的卡諾壓低眼簾,以為這樣便能藏起自己。
已經一個小時過去。
流理臺下提醒似的發出嗶嗶的鬧鈴音,打破靜謐。
卡諾像被拉回這個世界線,恍如隔世的神情,確認了下時間。
「姐姐還沒來呢。」我替她說出口。
「是阿。」她冷冷地說。
「如果你想離開,要先付清喔。」我說了,小小規矩。
她吸氣,吐氣。
一吸一吐的顫抖動作彷若體內沉著寒玉。
氣溫驟降,她開口。
「想不想聽個輝煌的故事。」
再好的關係間都有嫌隙,要是你自認沒這回事,那是還沒發生。
或者不想承認。
我愛我姊姊,同時,我也恨不得掐死她。
姐姐在外有個「英雄」的花名,那簡直像閃閃發亮的匾額,人們爭相抬轎般拱著。
相對的,我也有我的綽號。
「妖槍」卡諾。
對,我就是那把刺殺甘迺迪的槍,被人歧視活該是普世價值。
哈哈,有人想替我打抱不平嗎?你怎麼不試試消除人類對膚色的歧見。
人群總要有個共通的敵人才能齊聚人心,總要踩著別人分個高低才會感覺踏腳處穩妥。
噁心。
你問我為什麼要這麼負面,何不嘗試用積極進取的辦法對抗不公不義。
我沒有嗎?你以為我的星等為什麼比你們高?
好不容易在T02區點滴累計功勳,以為能夠反轉形象,來到新環境又後不付存在。
好累。
反倒是「妖槍」的舊瘡故態復萌,你實在管不了人群在你轉身後要談論什麼。
不夠努力?對,對,又是我,又是我的問題,是我不夠努力。
憤世忌俗是想為自己噴點文化香水,是無病呻吟,是我的錯。
好啊,我就來積極的消弭歧視。
危機就是轉機,對吧,要是姊姊不小心失誤,而我幫他擦屁股,那會怎麼樣呢。
「明天就是出擊的日子,還有一些設備沒有齊全。」姐姐用餐巾沾沾嘴角,即使在一般的餐館,她也散發五星級的禮儀,活脫是個用完鵝肝醬的貴族將領。
我們到基地附近的中華料理店作最後的戰前會議,店裡軍方成員不少,因為不久後格里芬預備與軍方開始合同作戰,基地裡也已有活躍的軍方人員。
這我無所謂,但不要一直看著這裡品頭論足,噁心的人類。
「我去借就好!」FN49舉手,怯生生地。
如果要我列個自卑排行榜,她肯定會在第一頁第一行第一個。
可惜我從來不適任安慰者的角色,我們倆湊在一起只會衍生更多負能量。負能量本來就只會疊加感染,不會因為跟人分享就移出一部份。
而且,很抱歉,接下來還得委屈委屈你。
「麻煩妳了,明天是我們第一次實戰,每個細節都至關重要。」我言不由衷。
隔壁桌的人類開始對我們擠眉弄眼。
嘖,真想早點離開。
「沒其他事我就先回去了。」我起身。
「這麼趕阿。」姊姊盯著我,直勾勾盯著我。
「有點事。」我不願跟她對上眼。
「有事?」
「有事。」
我一起步,隔壁桌的軍官便伸腳攔住我,金髮碧眼,身材魁武,神情自負,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身分似的把軍証擺在桌上。
我絆了上去,一個踉蹌。
「這也算戰術人形?文弱,看你的配槍,好像是很有名的那把喔。」他跟同袍們嘻嘻鬧鬧。
「不好意思。」我輕輕低頭,並擺手要姐姐不要發作,快步離開。
軍證已不在桌上。
「你好,這裡是軍證編號F85460015,請確認你們以下幾個設備的數量。」我撐傘走在回基地的路上,讀完代號,便將它彈進水溝。
「對,我全都要。」
這樣一來FN49就只借的到老式設備。
老式氣候測量儀非常好動手腳。
應該要是這樣的。
「請交由我來搬運!」FN49大聲道。
於是,我幾乎沒有充裕的時機碰測量儀。
即便如此我還是很草率的在清點設備時錯置了下系統,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用。
第一天任務結束時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我心裡想想算了,反正我就是繼續屈居人下,活在建築於謊言的世界之上吧。
然而任務區域內增加了預料之外數量的敵軍,似乎是還有別的小隊在附近行動。
而姐姐急公好義的個性也將小隊留了下來。
「我建議分成兩組,提高偵查敵軍的效率。」我舉手,刻意選了個不會被營火照亮臉的角度。
既然有第二天的機會,我也不會放過。
「馬卡洛夫,你怎麼看。」姐姐就是姐姐,要是我有所隱瞞,她也會特別敏銳。
「附議。」馬卡洛夫點點頭。
「我跟馬卡洛夫一組,姊姊跟FN49一組,分別在這兩個點待命。」
馬卡洛夫就是那種會穿上下一套格子睡衣的老派傢伙,偶爾會沉浸在紀律與榮譽的想像,像個嚴肅的傳教士向聽眾佈道。但也因此,她受人敬重,說話的份量和可信度很適合作一個見證者。
見證姐姐的小小偏誤與我優異的善後手腕。
第二天。
「數量有點異常阿。」馬卡洛夫舉著望遠鏡。
陰天,堅實的雲將悶雷困在天空,我渾身不對勁。
為什麼敵軍數量會這麼多?不是區區巡邏斥候嗎?
真不想知道原因。
「絕對有大人物在裡面,代理人?法官?夢想家?該不會是伊萊莎吧。」馬卡洛夫繼續分析。
沒事,姐姐看到這種數量也不會貿然開槍。
沒事沒事,怎麼可能出事。
「他們騷亂起來了!卡爾跟他們開戰了嗎?偏偏是這種沒用的通訊器。」馬卡洛夫。
姊姊一定已經發現測量儀有問題了。
我的小伎倆怎麼可能瞞過姐姐,我從來沒贏過姊姊阿。
沒事,一定是在有把握的情況下開槍的。
我拼命試著通訊器。
「嘖,偏偏不在我們的射擊範圍裡。」馬卡洛夫焦急。
「我要去救她。」我想吐。
「沒有通訊手段擅自離開只會增加會合難度,再觀察一下。」馬卡洛夫作出顯而易見地反駁。
沒事的,像第一天一樣,測量儀其實根本沒壞。
不會有事的,一定不會有事。
我握拳,指甲止不住摳著掌心。
拜託,為什麼是這種通訊器。
也許姐姐只是利用什麼幌子支開鐵血注意,向我們這徹過來了。
對阿,人家不是說,自己擔心的事,實際上七成不會發生嗎?
「卡諾!」
FN49的聲音!
我衝到窗口。
「卡諾!」FN49哭吼。
一個人。
我心都空了。
「沒錯,我就是人渣,反正我也不在意。」卡諾的淚水鼻涕爬滿了皺成風乾莓果般的小臉蛋兒。
我解開圍裙,繞過吧台,張開雙臂。
試著閃避的她幾乎摔下高腳椅,我穩穩用溫軟的懷抱捧住。
「不用說謊也沒關係喔。」我以替嬰孩拍嗝的輕柔勁道緩緩揉著她帶刺的心。
發燙的淚液滴入我的胸口,她終於將臉埋了進去。
「我真,的很對不,起。」她的字句被卡在喉頭的哀慟擠的次序不清。
但真心誠意。
「我知道喔。」
「對不,起。」
「好的好的。」
「可,不可以替我,跟姐,姐說我真的,很,對不起。」
「不可以喔,要自己說。」
「嗚嗚,我是真的,很對不,起。」
「我知道。」
「對不起。」
世界上的惡有很多種,常常被討論的是極端的必要之惡或純粹的惡。
但我們都忽略了觸手可及的無奈之惡。
我的意思是假若我經歷同樣的出生成長、社會壓力,也許也會在一個當下一個抉擇,做出同樣的判斷。
我常常覺得很難拿自己心中的尺,去丈量別人的善惡對錯,因為我不曾經歷她的經歷。她的心被社會堆塑為她不要的形狀,她被壓力逼出光怪陸離的行徑,她做出了惡人之舉。
這就是無奈之惡,在我眼裡。
太天真了嗎?太空泛了嗎?會姑息養奸嗎?
我不知道。
但我想抱抱這受傷的孩子。
她試圖持續以抽泣的身子吐著支離破碎的歉意,我使勁抱緊,令他沒有說話的餘裕,專注在宣洩淚珠的情緒裡。
在我閉上眼睛前,依稀望見流理檯下伸出的半隻胳膊。
那袖口彷若陽光蓬鬆的純白花朵,風雅工致的針線活層層展現縫製者細密的心。
她沒有打出什麼難懂的手勢,只是緩緩豎起拇指,像我懷裡的孩子。
顫抖不已。
《春田的酒吧軼聞》其貳:羅生門之鑰。
完。